歷史講評:也說“信”
歷史講評:也說“信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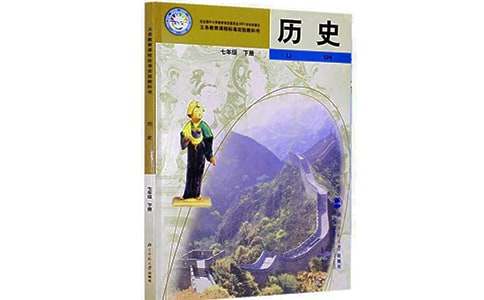
在《論語?顏淵》中有這么一段:
子貢問政。子曰:“足食,足兵,民信之矣。”子貢曰:“必不得已而去之,于斯三者何先?”曰:“去兵。”子貢曰:“必不得已而去,于斯二者何先?”曰:“去食。自古皆有死,民無信不立。”
于丹在其《〈論語〉心得》對之的解釋是:
沒有糧食無非就是一死,從古而今誰不死啊?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。最可怕的是國民對這個國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潰和渙散。
物質意義上的幸福生活,它僅僅是一個指標;而真正從內心感到安定和對于政權的認可,則來自于信仰。
這就是孔夫子的一種政治理念,他認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個國家凝聚起來。
她在這里將“信”解釋成“信仰”,并認為:這是“孔夫子的一種政治理念”,孔夫子“認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個國家凝聚起來。”
翻開商務印書館出版的《現代漢語詞典》,對信仰的解釋是:信仰,是指對人們對某種理論、學說、主義的信服和尊崇,并把它奉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和活動指南。
也就是說,如果于丹的這種“解釋”能成立的話,那么,孔夫子所說的“民”,對其統治者所提出的各種政治主張、所頒布的各種政令就應該是十分的了解,并且達到了信服和尊崇的程度,以致把它奉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和活動指南。但我們卻又知道孔夫子曾說過的另一句話: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。正好與于丹的這種“解釋”形成矛盾。事實上,在孔子時代,是不可能出現于丹所說的這種極端理想狀態的,早于孔子的管仲不就有《牧民》篇,把“民”等同于與牲口一樣的“牧”的對象嗎?作為把“克己復禮”視為自己最高追求目標的孔子,怎么可能與統治者唱反調呢?即便是現代社會,于丹的這種解釋也不過是理想而已,不然的話,我們就不會經常看到要求政府行政透明的呼聲見諸各種媒體了。
其實,在孔子時代是沒有“信仰”這個詞的,“信”也就不能解釋成“信仰”。其時,“信”通常是作兩種解釋。其一,是名詞,作誠信、信用解;其二,是動詞,作相信、信服、信賴解。例如,《論語?子路》中的“言必信,行必果”的“信”即是“誠信、信用”的意思;又如,與孔子同時代的《道德經》第十七章中的“信不足焉,有不信焉”,前一“信”就是名詞,后一“信”則是動詞;再如,孔子之后的商鞅徙木立信,為的也是在打造秦國統治集團信用的同時,使秦國民眾也確立誠實守信的做人準則。商鞅所求之“信”正是“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”的完美翻版。他要求秦民只需知道該干什么,而不能知道為什么要干。所以,當“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”時,“衛鞅曰:‘此皆亂化之民也’,盡遷之于邊城。其后民莫敢議令”。主
所以,筆者認為,“民無信不立”之“信”應作“誠信”解,而且是要求統治者先有“誠信”,從而使令民對之“信服”兩層意思,而非于教授所解的“信仰”。
諸君以為然否?
【也說】相關文章:
使用不必說也不必說單是造句06-28
「原創」也說人力資源07-02
也說“情人節”散文06-28
也說年終獎07-12
就算工作虐你千百遍,你也沒資格說分手06-30
寧愿憋死,也不要跟同事說這5件事!07-02
主管說寫離職報告也不批,說我礦工工資一分不給,如何應對?07-12
面試時候可以說我同學也在這個公司嗎?07-13
求職成也心態敗也心態06-22